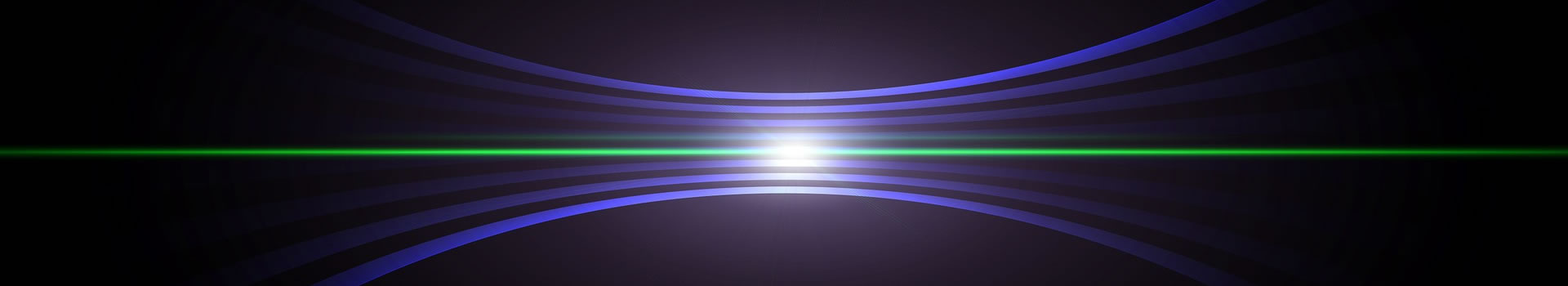
早晨六点,城市尚未统统苏醒。路灯在薄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,我站在考点校门外,呼出的白气蓦然被北风撕碎。目下是黑压压的东说念主群,千里默地蠕动着,像一条行将插足熔炉的锁链。羽绒服摩擦的沙沙声,行李箱轮子碾过冻土的闷响,还有压抑的、连三接二的咳嗽——这即是锻练第一日的序曲,果然得近乎粗粝,莫得半点肆意滤镜。

队列缓缓前移。手中的透明文献袋里,准验证上那张半年前的证件照显得有点目生。当时的目光里,八成还有更多不笃定。前边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女生,正反复默念着政事大题,睫毛上结了微弱的霜;右边一个男生仰头喝完临了一口黑咖啡,空罐子被捏得咔咔响。莫得东说念主交谈,一种渊博的、共振的颓落障翳着总共东说念主。这是二十岁年齿里,最自愿也最油滑的一次跋涉,一千个不同的梦,暂时挤在归并条实验的通说念里。

终于挪进教授楼。走廊里暖气的滋味混着古书的尘村炮扑面而来。找到座位,坐下,冰冷的椅子让东说念主一激灵。环视四周,前后摆布,大部分座位已有东说念主,埋头作念临了的冲刺。也有那么几个,桌面空空,准验证静静躺着——那是如故半途退场的梦思。铃声迫害地划破空气。试卷袋被阻隔的蓦然,教室里只剩下纸张摩擦的唰唰声,笔尖行走的沙沙声,还有我我方胸腔里过于使劲的心跳。时间像被冻住,又像在疯跑。写到临了一起解释题时,右手食指环节如故酸痛僵硬,窗外的天色,却鸦雀无声从千里重的铅灰,透出了一线白皙。
交卷铃响。走出科场时,脚步有些浮泛。外面的寰宇蓦然变得嘈杂而鲜嫩。有东说念主冲过来对谜底,语速赶紧;有东说念主沉默打理书包,眼眶发红;更多东说念主像我相通,仅仅长长地、无声地呼出连气儿,走进正午有些晃眼的、冰凉的阳光里。雪停了,地上留住杂乱的脚印,泥泞却坚实。

第一战为止了。它不像思象的那么壮烈,更像完成了一次必须的泅渡。未来还有硬仗,但此刻,至少我抓住了运说念的笔,在芳华的考卷上,写下了第一滑窒碍涂抹的谜底。这场一个东说念主的干戈里,每一个走到今天的东说念主,皆已是我方的英豪。而路的止境,雪正渐渐溶解,夸耀地面原本的神色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