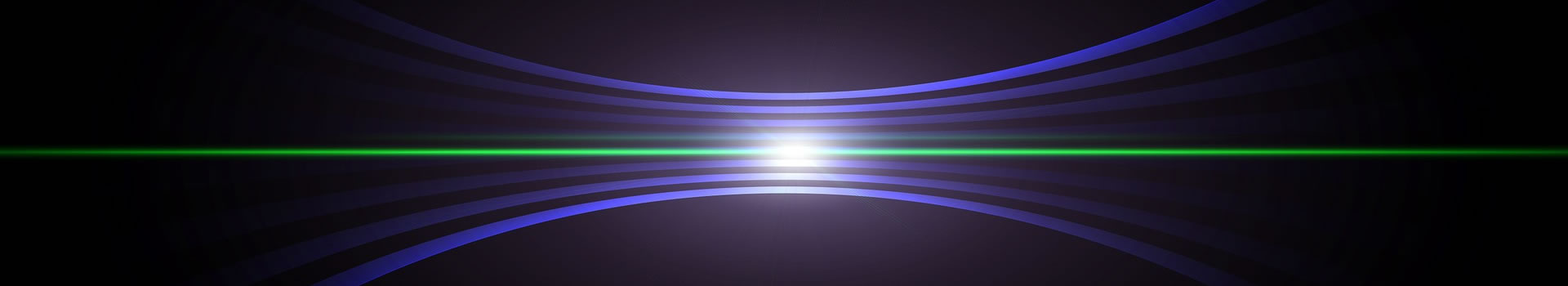
风急霜寒木叶稀,菊花开遍欲霏微。
雁横秋水山容瘦,蝉噪斜阳岭色归。
佳节乍逢双日月,浮生浑过两京畿。
酒酣不觉凭栏久,落照空梁燕子飞。

这首七律以重阳节令为布景,通过深秋景物的层层铺陈与东谈主生况味的狭窄表露,构建出悲惨与渴望交汇、感叹与哲想并存的田地。
诗中既有“风急霜寒”“雁横秋水”的肃杀之景,又暗含“菊花开遍”“酒酣凭栏”的人命韧性,最终以“落照空梁”的暮色收束,传递出对时光荏苒与人命归处的深千里叩问。

首联“风急霜寒木叶稀,菊花开遍欲霏微”
以凛凛的笔触开篇:疾风裹带寒霜,木叶雕零成稀,深秋的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
而“菊花开遍”却如芒刃破开寒色,在凋零中洞开出倔强的渴望。
但“欲霏微”三字突然飞舞——花虽盛,终将随霜露隐匿,既写目下之景,又暗喻人命平和的少顷性,酿成冷与暖、生与灭的强烈张力。

颔联“雁横秋水山容瘦,蝉噪斜阳岭色归”
进一步拓展画面:雁阵掠过寒水,山峦在暮色中显出清癯的轮廓;蝉鸣点破斜阳的寥落,岭色随日影西千里而渐次昏黑。
这里“横”与“噪”赋予当然以动态的人命力,而“瘦”与“归”则暗含时光侵蚀的陈迹——山因秋而瘦,岭因暮而归,实则是目之所及处,万物都在走向衰微。

颈联“佳节乍逢双日月,浮生浑过两京畿”
由景入情,将视角从当然转向东谈主事。
“双日月”既指重阳节令的独特天象,又暗喻岁月近似的糊涂感;“两京畿”以长安、洛阳两座帝都的隆替,隐喻东谈主生如漂荡的孤舟,在运谈的河谈中昏头昏脑地流徙。
这一联将节日的少顷欢愉与半生的蹉跎并置,酿成强烈的情谊落差。

尾联“酒酣不觉凭栏久,落照空梁燕子飞”
以场景收束:酒至半酣倚栏眺望,暮色中的房梁萧然无东谈主,只须燕子掠过残照。
此处“不觉”二字极妙,既写陷落忘时的痛惜,又暗指东谈主生常在无果断间错失良辰;而“空梁”与“燕飞”的对照,既是物理空间的萧瑟与生灵的少顷栖居,亦隐喻着东谈主如秋燕,终将离巢远行却难觅归处。
残照中的这一幕,将全诗的悲惨推向极致,却又在寥落中透出一点超然的顿悟。

这首诗以重阳秋色为经纬,将当然预见的强烈与东谈主生况味的钝痛详细交汇。
从饱经世故木叶的肃杀到菊花的倔强洞开,从雁阵蝉鸣的动态到山峰暮色的千里静,再到节日欢愉与半生漂荡的对照,最终在酒酣落照的空庭中完成对人命实质的叩问。

诗中既有对时光荏苒的痛切感知,又有对存小心旨的腌臜追寻——菊花的“霏微”、燕子的“飞”,都是人命在阑珊与破碎中的势必轨迹,而暮色中的凭栏者,终在注视这一切时,与无常的运谈结束某种巧妙的息争。

